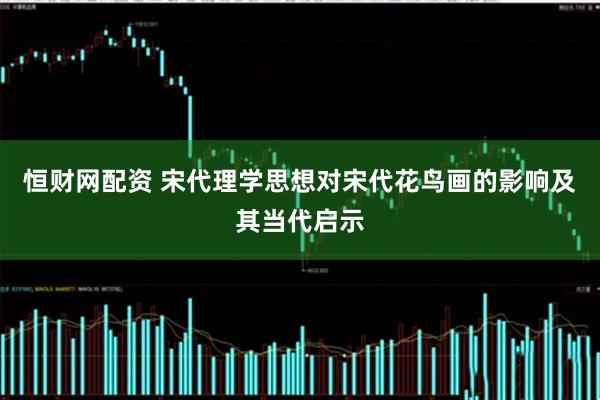
摘要
宋代花鸟画在中国绘画史上达到艺术巅峰,其成就不仅体现在精工写实的技艺层面,更在于深刻的文化内涵与独特的意境营造。本文聚焦宋代理学思想与花鸟画艺术的互动关系,系统探讨“格物致知”哲学如何塑造宋代花鸟画的审美范式,并分析其对当代花鸟画创作的启示意义。
研究指出,宋代理学强调“即物穷理”,推动画家以科学态度观察自然,追求“形似”与“神似”的统一,使花鸟画由单纯的视觉再现升华为“以物观道”的精神实践。通过《芙蓉锦鸡图》《枇杷山鸟图》等经典作品分析,揭示其“格物”精神与“意境”表达的辩证统一。针对当代部分画家重“形”轻“意”的倾向,本文主张回归宋代“理—象—意”三位一体的艺术传统,倡导在继承“格物”写生精神的基础上,强化作品的哲理深度与人文关怀,实现传统美学的创造性转化。宋代理学所倡导的“天人合一”理念,仍为当代花鸟画超越技术主义、重建精神家园提供根本路径。
关键词:宋代花鸟画;宋代理学;格物致知;意境;当代创作;艺术传承;文化精神
展开剩余86%一、引言:鼎盛之源与当代之困
花鸟画作为中国传统绘画的重要门类,自唐代独立成科,经五代发展,至宋代达到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。宋代花鸟画以其精微的写实技巧、严谨的构图法则与深邃的意境营造,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典范。其成就不仅在于技艺的成熟,更在于与时代思想的深度融合。北宋中期以降,以程颢、程颐、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思想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,其核心命题“格物致知”“理一分殊”“天人合一”深刻影响了文人艺术的审美取向。
在这一思想背景下,花鸟画不再仅仅是装饰性或娱乐性的技艺,而被赋予了“体道”“明理”的文化功能。画家通过对一花一鸟的细致观察与艺术表现,试图揭示宇宙万物背后的“理”,实现个体心灵与天地精神的共鸣。这种“以物载道”的艺术追求,使宋代花鸟画兼具科学精神与诗意境界,形成了“形神兼备、理意并重”的独特范式。
然而,进入当代,部分花鸟画家在追求技术精进的过程中,陷入“唯技是图”的困境:过度强调形态的逼真、技法的繁复,却忽视了传统绘画中“气韵生动”“意境深远”的核心价值。画面虽工,却失之于匠;形象虽似,却寡于情思。这一现象暴露出对传统艺术精神理解的片面化。
本文旨在从“格物”与“意境”两个维度,深入剖析宋代理学思想对花鸟画的塑造机制,并探讨其对当代创作的启示,以期为花鸟画的当代发展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路径。
二、格物致知:理学思想下的写实精神
宋代理学的核心命题之一是“格物致知”,出自《礼记·大学》:“致知在格物,物格而后知至。”程朱学派将其发展为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,强调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深入观察与研究,以通达普遍之“理”。朱熹释曰:“所谓致知在格物者,言欲致吾之知,在即物而穷其理也。”
这一哲学理念深刻影响了宋代绘画,尤其是花鸟画的创作实践。
(一)“即物穷理”的创作态度
宋代画家普遍秉持“对花写照”“对禽摹形”的写生传统。《宣和画谱》载:“画花果鸟兽,即以生样为祖本。”画家需长期观察自然,记录物象的形态、结构、习性与生态关系,力求“曲尽其妙”。
如宋徽宗赵佶《芙蓉锦鸡图》中,锦鸡羽毛的排列、光泽、动态均符合红腹锦鸡的生物特征;林椿《果熟来禽图》中,枇杷叶的虫蚀痕迹、果实的成熟度、枝叶的承重弯曲,皆细致入微,显示出对植物生长规律的深刻理解。这种精确性并非机械复制,而是“格物”精神的体现——通过观察个体之“分殊”,体悟生命之“大理”。
(二)“形似”与“神似”的统一
理学强调“理”寓于“物”中,故“形似”是通向“神似”的必经之路。但“神似”并非止于外貌,而是对物象本质特征与内在生命力的把握。
崔白《双喜图》是典范之作。画面描绘野兔惊觉回首,双鹊振翅鸣叫,风动草木,气氛紧张。画家不仅准确描绘了动物的解剖结构,更捕捉了其瞬间的心理状态与生态互动,使画面充满戏剧性与“生意”。这种“神似”,正是“格物”之后的“致知”——对生命律动的深刻体认。
(三)“理法并重”的形式规范
“理”不仅指自然之理,亦含艺术之理。宋代画院在徽宗主持下,建立严格的创作规范,要求画家“形似”为先,笔法严谨,设色典雅。这种“法度”并非束缚,而是“理”的外化,确保艺术表达的秩序与和谐。
如吴炳《竹雀图》,雀鸟立于竹枝,三只姿态各异,顾盼生情。构图遵循“三远法”与“黄金分割”,枝叶穿插有序,色彩清雅,体现出高度的形式控制力。这种“法”与“理”的统一,使作品既真实又理想。
三、意境营造:理学观照下的精神超越
“格物”是手段,“致知”是目的,而最终指向的是“意境”的营造——即超越物象本身,传达哲理、情感与宇宙观。
(一)“以物观道”的象征表达
理学认为“万物皆有理”,花鸟不仅是观赏对象,更是“天理”的显现。画家常借物抒怀,赋予花鸟以人格化象征。
如赵佶《芙蓉锦鸡图》题诗:“秋劲拒霜盛,峨冠锦羽鸡。已知全五德,安逸胜凫鹥。”锦鸡被赋予“文、武、勇、仁、信”五德,成为君子人格的化身;芙蓉“拒霜”象征坚贞不屈。二者结合,构成“比德”式图景,体现了儒家伦理理想。
此类象征在宋代花鸟画中广泛存在:梅喻高洁,兰喻幽贞,竹喻劲节,菊喻隐逸。这些意象虽在元代“四君子”题材中定型,然其思想根源已在宋代理学影响下萌芽。
(二)“天人合一”的境界追求
理学最高境界是“天人合一”,即个体心灵与宇宙精神的融合。花鸟画通过“小中见大”的构图与“计白当黑”的留白,营造空灵意境,引导观者超越有限物象,进入无限宇宙。
如佚名《出水芙蓉图》,一朵荷花占满画面,背景全白。花瓣层层叠叠,粉白渐变,露珠晶莹,呈现出“出淤泥而不染”的纯净之美。画面无诗无款,却令人联想到周敦颐《爱莲说》的文脉,引发对生命本质的哲思。这种“无声之诗”,正是“天人合一”境界的视觉呈现。
(三)“平淡天真”的审美理想
理学尚“诚”“敬”,反对矫饰。在艺术上体现为“平淡天真”的审美趣味。画家追求自然流露,不事雕琢,以简驭繁。
如梁楷早期工笔作品(传)或马远、夏圭的花鸟小品,构图简洁,笔墨洗练,意境幽远。这种“简”非贫乏,而是“绚烂之极归于平淡”的哲学表达,与理学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的修养论相呼应。
四、对当代花鸟画的启示:从技术回归精神
当代花鸟画在材料、技法、题材上均有拓展,然部分作品陷入“重形轻意”的误区:追求超写实效果,却缺乏精神深度;模仿传统图式,却失去文化语境。这一困境的根源,在于对“格物”与“意境”关系的割裂。
(一)重拾“格物”精神,避免程式化
当代画家应继承宋代“即物穷理”的写生传统,深入自然,观察真实生态,避免闭门造车与符号复制。唯有“真”,方能动人。可结合摄影、标本、生态记录等现代手段,拓展“格物”视野。
(二)强化“意境”表达,超越技术主义
在“形似”基础上,应追求“神似”与“道似”。作品应承载现代人文关怀,如生态保护、生命哲思、文化记忆等。可通过象征、隐喻、诗画结合等方式,增强作品的思想厚度。
(三)重构“理—象—意”三位一体的创作观
当代创作应重建“理”(哲理)、“象”(形象)、“意”(意境)的有机统一。以“格物”为基,以“致知”为导,以“意境”为归,使花鸟画不仅“好看”,更“耐看”“深思”。
五、结语:传统的重量与未来的方向
宋代花鸟画之所以成为艺术高峰,正因其将理学思想内化为艺术精神,实现了“技”与“道”的完美统一。其“格物致知”的写实精神与“天人合一”的意境追求,构成中国传统绘画的核心价值。
面对当代艺术的多元化挑战,花鸟画的发展不应是简单的复古或彻底的颠覆,而应是一场“返本开新”的文化实践。唯有深入理解宋代花鸟画在理学影响下形成的审美范式,方能在继承中创新,在创新中延续文脉。让古老的花鸟意象,在当代语境中继续承载哲思、传递情感、安顿心灵,这才是对传统最深刻的致敬。
文章作者:芦熙霖(舞墨艺术工作室)
发布于:北京市淘配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